摘要 有两件事,田永君的妻子特别不理解他。其一是,20来年只干一项工作竟不觉得烦闷。从“是否存在比天然金刚石更硬的材料”,到“到底能制造出多硬的纳米金...
有两件事,田永君的妻子特别不理解他。其一是,20来年只干一项工作竟不觉得烦闷。从“是否存在比天然金刚石更硬的材料”,到“到底能制造出多硬的纳米金刚石基的人工材料”,他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硬度的面纱”。在他眼里,这个漫长而又耗费耐心的过程好比星球探秘,“每前进一步,都能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其二是,对通宵打牌的无限热情。他喜欢打扑克牌,但不是和什么人都打。牌友跟他一样也多是“杰青”,哪怕远隔千里,只要一声招呼,便直奔而去。据他描述,这样的牌局常有4到6人,与钱无关只拼技术,有时可以不眠不休“连续作战”。他笑言:“科学家也需要‘放飞自我’。”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德国洪堡学者……而今,燕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永君的头衔又多了一项“2016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得主”,“我很幸运,喜欢的和从事的,刚好是同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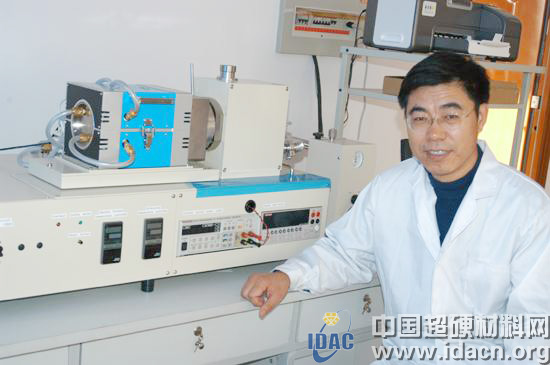
54岁的田永君就像个矛盾综合体。
他尊称学界的前辈为“先生们”,每每提及,总会挺直腰身、一脸崇拜。谈到妻子必是“我夫人如何如何”,言辞敬重。
他用老年款手机,只有收发信息和接打电话的功能。偶尔也看电视,但只爱战争剧。
尽管学术成就斐然,但他不喜欢任何“露脸”的机会。他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是在11年前,即是献给了河北日报。
他总说生活和工作要分开,家中甚至不通网线,更没有WiFi,“这样处理电子邮件就必须去办公室了。”但他的大脑却做不到如此泾渭分明,“科研之于我,正如手机之于你,饭后睡前、坐车排队,处处都是可以抓紧思考的时间。”
田永君并不是“古板学究”,他会说“年轻人的话”,也爱把生活里的幽默讲成段子。
记者问:“当初为何投身学术?”
他答:“被父亲逼的,本来我有机会从政的。”
高考填志愿,田永君的父亲千挑万选,给他报了金属材料热处理专业,“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听上去应该好就业。”
事实的确如此。他读的是哈尔滨科技大学,既是党员,成绩又拔尖,毕业后极有希望去企业。可毕业分配时,父亲却改了主意:“思来想去,还是书斋里安静,你就继续读书吧。”
父命不敢违,已经准备好去社会上打拼的田永君只能突击考研。1987年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94年,他又进入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博士学位,后获德国洪堡奖学金,漂洋过海孜孜求学,“一步步被逼上了科研的‘不归路’。”
但他还是回来了。1998年,田永君回到燕山大学,随后开始筹备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省级重点实验室,2006年实验室正式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期间,他成为河北省首位“长江学者”。
“我有个特点,不管干什么,只要选择了就能一门心思钻进去。就像当初报专业,虽然之前都没听说过,但学就要学好。凡事都有它有趣的一面,但你必须沉下心才能有发现。”田永君说。
他至今难忘大学生活的恣意洒脱。他把自己归为比赛型选手,想当年,长跑、篮球等竞技类项目样样在行,尤其喜欢挑战高手。“现在年纪大了,大球不打了,就找体育学院的足球老师比羽毛球。”他狡黠一笑。
他的照片极少。前不久评奖时需要几张生活照,他在家中翻箱倒柜只找到两张1寸证件照,只得无奈寄出。即便是跟家人一起出游,他也很少出镜,“大概是因为我长得丑吧。”
他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当过兵,“我父亲就是军人出身,印象中他年轻时的腰板就没打过弯。我特别喜欢军人那股‘硬汉’的劲儿,这点倒跟知识分子的气节有点相通。”
“我不愿做追随者”
怎样寻找更硬的新材料?过去,科学家们使用的方法常被称为“炒菜法”,即只有做出来后,才能品评它们在“色、香、味”上的差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
早在1934年,英国学者就曾在一本专著中无奈地写道:“硬度就像大海的暴风一样,容易理解,但不容易度量。”直到1998年,美国物理学家仍在慨叹:“硬度不仅仅是难以度量的,而且是难以定义的。”
田永君偏偏要挑战不可能。“要么去攻克公认难题,要么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两条路最难走,风景却也最诱人。除此之外,即便在他人开拓的方向上更努力地奔跑,最多也不过是追随者中的前几名。我不愿做追随者。”
1999年,田永君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员开始探索在硼、碳、氮三元材料体系中寻找合成新型超硬材料的可能性。刚一开始,他们便面临那个困扰学界的世纪难题:如何在原子层面上对新型超硬材料进行设计。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2003年,美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刊发了来自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省级重点实验室的文章《共价晶体的硬度》,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必事先合成,我就知道谁比谁硬。”
在田永君看来,成功的原因无外乎兴趣、坚持、运气和天分,“有时候,那么一点点灵感的确能让研究事半功倍。”灵感是拿时间换来的。除了大年三十,他几乎每天都去实验室报到,有时要盯实验,有时只是转转。前不久因高烧在家休息,他吃完药躺在床上高兴极了,“就像把一台连续运转的超负荷电脑强制关机,整个人都放松了。”
巧解难题,田永君只用了一组公式。“你看多奇妙,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竟然用几个字母就说清了。用简单揭示复杂,这便是科学的美。”
最近几年,他和研究团队又依据公式相继合成出超细纳米孪晶结构的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块材,两种材料的硬度、韧性和热稳定性三大性能指标同时得到提高,其中纳米孪晶结构金刚石的硬度2倍于天然金刚石,“用其制造的刀具,已经实现了淬硬钢的镜面加工。”
如今,田永君三言两语就介绍完的研究成果,当初却也让他挠头抓瞎:“我们合成了比天然金刚石更硬的新材料,可谁能把它切割成使用所需的形状和大小呢?”他心下茫然,而此时同行们甚至还不相信已有这样的研究飞跃,“只能发动各种资源找、试,最终才锁定了飞秒激光。”
他还记得出成果那天,团队成员们虽然激动却很克制,“研究又不是到此止步,喝一顿小酒也就把这事儿翻篇了。”
“不能让人家白交学费”
除了“科学家”,田永君对他的另一个身份——“授业者”,也不容半点马虎。这点从他研究团队的师生比上可见一斑:7名教师一年只招6名博士生,高校中少见的倒梯形结构。
“学校分配给我们‘杰青’和‘长江’的名额,是每人每年可招2至3名博士生,但招生不是凑数,要看他适不适合科研、适不适合这一领域,宁缺毋滥。”他的观点很朴素,一个家庭要耗费很多心血才能下决心让孩子读博士,“我们不能让人家白交学费。”
他提倡一种更自由的“精英式”教育。6名学生每人都配有一名理论指导老师和一名实验指导老师,从学术和实践两个方向对其进行指导。所谓的“我的导师”只是各种必填表格中的一个名字,实际上,他们可以推开课题组里任何一位老师的办公室大门,将自己的科研困惑和盘托出、寻求帮助。
“时间长了,老师们常常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的学生,这样也好,没了门户隔阂,不管是谁推门进来都有教无类。”田永君说。
但“散养”并不意味着可以更轻松。
田永君有位博士生围绕某化学元素研究多年,初有新发现时便心切地想要发文章,被他泼了一瓢冷水:“结论确实吗?能重复吗?你有几成把握?”在他看来,对于新发现至少要先保证自己“做一个、成一个”,再把新现象背后的物理起因搞清楚。最终,这篇论文被他们足足磨了8年。
“严”的效果很明显。有一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河北省有3篇入选,其中,田永君参与指导的就占2篇。而今提起他的学生,许多都在世界一流学府继续深造,“学生成材,我心甚慰。”(记者张怀琛)


 手机资讯
手机资讯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豫公网安备41019702003646号
豫公网安备41019702003646号